结婚制度的沿革
结婚制度的沿革结婚制度是个体婚制的产物,它在历史上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

(一)早期型结婚方式举例
这里早期是指个体婚制形成时期。
当时主要有掠夺婚、互易婚、劳役婚、买卖婚、赠与婚等。
掠夺婚亦称抢婚,指男子以暴力掠夺女子为妻,这种结婚方式大致出现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时期。
掠夺婚是以强行“掠夺”的方式达到成婚目的的一种婚姻仪式。
它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
我国云南的景颇族、僳僳族和傣族还留有掠夺婚的野蛮习俗。
一般夺婚之前,男女已经有了爱情关系,相互约定时间和地点,男子抢夺时,女子装出呼救姿态,通知家人和邻里营救,这时男子或设法逃走,或把女子抢走,再派媒人正式向女家求婚,付出一定彩礼。

历史
掠夺婚俗称抢婚,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制时期的一种强制性的婚姻形式,后来在不少民族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逐渐由真抢变为假抢。
《易经归妹》:匪寇婚媾.有人认为寇与婚媾截然不同,将其混在一起可能说明古代的婚姻与寇密切相关,即认为寇与婚并提,应是掠夺婚的体现。
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的乌桓族盛行这一婚俗。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族的婚俗是:先掠女子同居,半年或百日之后,送牛、马、羊至女家作为聘礼。然后男子随女子至女家,给女家服役一、二年。之后,女家送一份厚礼给女儿,包括双方住宅、结婚用品,均由女家负责。乌桓族的这种婚俗具有多元性,它既是劫夺婚的形态,也有服役婚的内容。

互易婚亦称换婚,指双方父母互换其女为子妇,或男子互换其姐妹为已妻。
劳役婚指男方须为女方家庭服一定时期的劳务,以此作为与女方成婚的代价。
买卖婚指男方向女方家庭给付金钱或其他等价物,以此作为与女方成婚的代价。
赠与婚指有主婚权的父母、尊长将女赠与他人为妻,并不索取代价。它不同于买卖婚,但女子仍处于赠与标的物的低下地位。
其中,掠夺婚、赠与婚可称为无偿婚,互易婚、劳役婚、买卖婚可称为有偿婚。

(二)中国古代的聘娶婚
这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结婚方式,盛行于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男家娶妇(男子娶妻)须向女家依礼聘娶。
所谓“六礼”,便是聘娶婚中的嫁娶程序,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
“纳采”反映男家遣媒人携带礼品赴女家提亲。
“问名”指男家遣媒人查明女子的生辰八字以及女子生母的姓名,以备占卜。
“纳吉”是指男家在此项婚事卜得吉兆后告知女家,以示庆贺。“纳吉”亦称文定,一般均在此时写立婚书。
“纳征”指男家向女家交付聘财。女家收纳聘财后,婚约即告成立。
“请期”指男家向女家请以完婚之期;在男家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形下,往往沦为“告期”。
“亲迎”指完婚之日男家往女家迎娶,迎归后行“合卺”之礼以示成妻。
此外,女子嫁入夫家后还须行成妇之礼。
经“庙见”后,始得成为夫方宗族的成员。
“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登于祢,成妇之义也。”如果女子未经庙见而死,只能“归葬于女氏之党”。
“六礼”之制历代数有变迁,后世不及早期严格,渐有简化之势。宋代改“六礼”为四,即“纳采”、“纳吉”、“纳征”、“亲迎”。<朱子家礼)中将“纳吉”并入“纳征”。
元代增“议婚”一项。明、清时期基本上沿用(朱子家礼)。
历代的户婚律均以写立婚书、收受聘财为定婚条件。
在实际生活中,王公、高官等上层人物多行古礼,庶民百姓的嫁娶程序则较为简略。

(三)古代各国的宗教婚
宗教婚盛行于古代各国,许多宗教经典都有关于结婚方式的要求。
市民法上的共食婚便是古代罗马的一种宗教婚,婚礼由神官主持,结婚当事人共食祭神的麦饼后,婚姻始得成立。
印度教的(摩奴法典)规定了八种结婚方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种姓的人。其中类似买卖婚姻的,被称为阿修罗的结婚方式。
按照伊斯兰的教义,结婚是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但不得与异教徒结婚。结婚以前,男方须向女方之父交送“麦尔”或“沙对”。
成婚之日,举行由阿訇主持的宗教仪式。
欧洲中世纪是基督教的全盛时期。许多国家以基督教为国教。
按照寺院法对形式要件的要求而成立的宗教婚,是当时最主要的结婚方式。
结婚被视为七项圣典(亦称宣誓圣礼)之一。结婚须向当地教会申请,事先经教会公告。婚礼由神职人员主持,当事人须宣誓并接受神职人员的祝福。
中世纪以后,基督教的宗教婚逐渐为民事婚所取代,但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

(四)近现代的共诺婚
共诺婚亦称合意婚,依男女双方的结婚合意而成立,一般采取民事婚的方式。共诺婚制是在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到资本主义婚姻家庭制度过渡的时期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
在结婚方式上,首先采用选择民事婚制度的是16世纪的尼德兰(即今之荷兰)。所谓选择民事婚,是指依宗教的方式结婚还是依民事的方式结婚,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经上述两种方式而成立的婚姻均为有效。
17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也在敕令中肯定了选择民事婚制度。
法国大革命后,1791年的宪法指出:“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规定:“未经合意不得成立婚姻。”此后,欧洲各国在立法上相继进行了结婚方式的改革。但是,这种改革是渐进的。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共诺婚制的确立,民事婚成为普遍通行的结婚方式。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共诺婚,在价值观上是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原则相一致的,是以契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
婚姻既为契约,当然须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成立条件。这同无视或漠视当事人结婚自由的古代婚姻相比较,无疑是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自愿并不能消除社会条件对结婚自由的限制。
20世纪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结婚法作了修改,法定的结婚方式趋于简化。
原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均以依法办理登记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

(五)中国百年来结婚方式的演变
中国结婚法的近代化始于20世纪之初。
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期制定的民律草案,既有对资本主义国家婚姻制度包括结婚方式的模仿和借鉴,又有对本国旧制的沿袭。
由于均未施行,北洋军阀时期对结婚的法律调整,仍然是以《大清现行刑律》中的有关规定为依据的。
当时的大理院还作过解释和判例,如订婚须写立婚书,依礼聘娶,结婚须有合法的主婚人主婚等,使传统的结婚方式得以延续。
1930年公布、1931年施行的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以仪式婚为法定的结婚方式,结婚须举行公开仪式,并有二人以上之证人证明。
实际生活中传统的聘娶婚仍然流行,只是在方式、程序上有所简化。
中国的新民主义婚姻制度发端于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婚姻制度的改革也包括结婚方式的改革。
各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法、婚姻条例均规定,男女结婚须办理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以结婚登记为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
这种首创的结婚登记制度,在建国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均规定,结婚当事人须向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以此作为结婚的法定方式。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原内务部和民政部在不同时期都颁行了婚姻登记办法或条例,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是自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

我国婚姻法律对事实婚姻处理方式的发展
事实婚姻是相对于合法登记的婚姻而言的,事实婚姻未经依法登记,本质上属于违法婚姻,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为了维持一定范围内的,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婚姻关系的稳定,国家对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双方之间的关系有条件地予以认可,这就产生了“事实婚姻”这一概念。在具体分析五个阶段前,我们来分析事实婚姻成立的要件,再去深入理解其发展,目前,事实婚姻成立的要件有:
1.有同居行为。但必须是男女双方在一起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且该同居行为始于1994年2月1日以前。
2.事实婚姻的男女必须是以夫妻名义进行同居。
3.时间要求。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必须是在1994年2月1日(不含2月1日当天)之前就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该日期之后,男女双方必须办理结婚登记才能确立夫妻关系。
4.男女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前同居时,已经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所谓结婚的实质要件即男女双方建立夫妻关系必须具备的条件,具体包括:
(1)双方均达到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
(2)双方自愿结婚;
(3)双方均无配偶且不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4)双方均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5.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在离婚诉讼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的,之前的同居关系溯及地产生效力,可以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未补办结婚登记的,只能以同居关系对待,不存在事实婚姻。
事实婚姻的成立要件使得事实婚姻与同居等得以区分。
自建国以来,我国在不同的阶段对事实婚姻的处理作出了不同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不断出炉更新。站在不同的角度与标准,对我国事实婚姻的处理演变过程也有不同的认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曾数次对处理事实婚姻的处理经历了有条件的承认到不承认主义再到相对承认主义的发展过程。由于历史传统、公民法律意识等诸多因素,事实婚姻在我国大量存在,从有利于家庭稳定,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出发,有条件的承认事实婚姻符合现实国情。
总的来说,从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事实婚姻行为经历了从绝对承认、相对承认到绝对否定、相对承认主义、逐渐完善的《民法典》时代阶段。

深入理解了要件,有利于我们对五个阶段划分的理解,下面是对五个阶段的分析:
第一阶段,绝对承认阶段:
(建国初期)
我国建国以来1950年颁布第一部《婚姻法》,其中明确规定登记为法定婚唯一要件。然而由于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没有进行登记的婚姻,使得立法这不得不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调和理论和实践冲突的规定。
在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制定了《有关婚姻问题的若干解答》,其中“在婚姻登记机关已建立而不去登记结婚是不应该的”表明,立法者并没有强制事实婚姻的绝对无效,只是对事实婚姻采用了一种消极的态度——不鼓励。由于立法者也没有强制事实婚姻的双方必须到登记机关去登记,于是现实中事实婚姻现象普遍存在。
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中首次对事实婚姻提出了概念性解释,提出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群众认为是夫妻的行为。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要坚持结婚必须进行登记的规定,不登记是不合法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处理具体案件要根据党的政策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双方已满结婚年龄的事实婚姻纠纷,应按一般离婚案件处理。从这个意义中可以看出立法者实际上是认可事实婚姻的,将事实婚姻最为合法婚姻处理,当双方发生纠纷时以离婚案件处理。尽管1980年修正了旧《婚姻法》,但是在1984年的司法解释中仍坚持了上述意见中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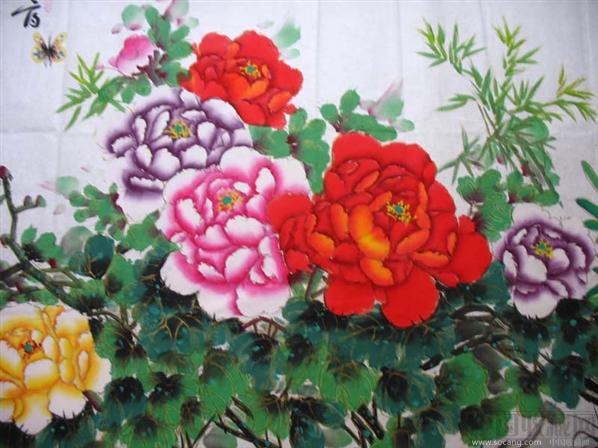
第二阶段,相对承认阶段:
(1989年11月21日到1994年2月1日期间。)
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
(1)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以前,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起诉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起诉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2)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以后,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第三阶段,绝对否定阶段:
(1994年2月1日起至2001年4月28日期间。)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发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并且规定对于起诉到法院,应按照非法同居关系对待。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期间立法者完全否定事实婚姻制度。或许是现实中有太多的事实婚姻,法律难以杜绝此现象时立法者不得不采用强制手段来归制这些欠缺形式要件的婚姻。

第四阶段,相对承认阶段:
(2001年12月26日)
2001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解释(一)》)
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时算起。
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自2001年12月26日起,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者经补办登记,其同居关系可溯及既往地合法化,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如果双方不补办结婚登记,其关系视为同居关系,不视为事实婚姻。

第五阶段:《民法典》时代下,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兼顾了回归与革新的立法理念。
基于婚姻家庭法对民事法律体系的重新融入,婚姻家庭编明确了其基本原则体系相对于民法典总则的独立性,并对身份法律行为建立起三层次的规则适用体系。立法者重新重视家庭法律结构,提出了家庭法律关系的倡导价值,明确了近亲属和家庭成员的范围,强化了家庭关系的“国家认可”标准。夫妻财产规则基于家庭财产结构的变迁发生了与时俱进的革新,新增了夫妻债务认定规则、婚内夫妻财产分割规则、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则、家务劳动补偿规则等内容。在“疏堵平衡”的指导思想下,婚姻退出机制得到了人性化的完善,如疾病婚姻被调整为可撤销婚姻,登记离婚适用“冷静期”制度等。
和“事实婚姻”相关的具体条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婚姻家庭的禁止性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一千零五十四条【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随着社会法治化的建设,人们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已经很少会看到结婚不登记的情形,但是在以往的一些法律意识尚浅的地区,婚姻登记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根本无视婚姻登记的法律制度。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结婚应当登记。经婚姻登记机关合法登记后的婚姻关系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而那些未经婚姻登记机关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情形,便是我们所称的事实婚姻。虽然《民法典》施行后《婚姻法》废止,那么《婚姻法》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成为无源之水。但是法律对于“事实婚姻”态度应该并没有发生变化,即1994年2月1日以后的“事实婚姻”按同居关系处理,当事人不享有继承权、扶养权等夫妻权利。而对1994年2月1日以前的“事实婚姻”,法律承认其婚姻法律效力,与合法婚姻一样收到法律的保护。
从事实婚姻的要件和内容来看,我国对事实婚姻的处理和发展离不开经济水平的提高、法律制度的完善、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等等,和现实中的社会习惯的变化也密切相关,这涉及到了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及其解除后果的问题:

1.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1)从人身关系方面的内容。
事实婚姻对人身关系的效力即对双方当事人及对子女的抚养产生的法律后果。根据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凡被认定为属于事实婚姻关系的,实际是确认其婚姻关系有效。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事实婚姻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具有夫妻身份,彼此间的关系适用婚姻法关于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如互负抚养义务、双方所生的子女为婚生子女、互有配偶继承权。事实婚姻关系的子女具有与合法婚姻关系的子女相同的法律地位和权利。
(2)财产关系方面的内容。
事实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与登记设立的夫妻关系具有同样的内容。例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另有约定除外;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和收益权等。

2.事实婚姻的解除
事实婚姻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在登记立案后,应根据《婚姻法解释(一)》《婚姻法解释(二)》的规定办理,不能一见到未办结婚登记的就一概认定为同居关系,只要符合事实婚姻构成要件的,可认定其具有事实婚姻的效力,不必再自行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按离婚案件处理;同时在处理事实婚姻案件时,对事实婚姻中的男女,如果一方坚持离婚,经调解无效后,法院应当判决离婚,不能判决离婚,这也是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的显著区别。
对不构成事实婚姻的,应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办理:
“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出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也就是说,法律对同居关系的解除与否不予干预,只对当事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的予以受理,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案件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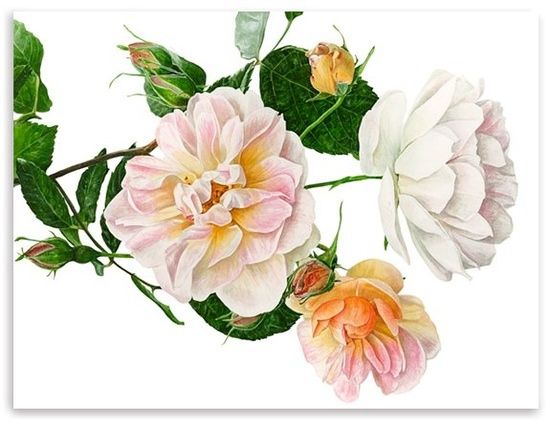
3.解除案件事实婚姻关系时财产分割的效力
对于财产的分割,如果双方之间订立有协议,就按照协议的约定办理;如果双方之间不存在协议,则在解除事实婚姻关系时,对于财产的分割,按照夫妻共同财产来分配,则适用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有关规定。
按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根据上述原则,事实婚姻双方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根据财产的不同性质来进行财产分割:原则上,一方的个人财产仍归个人所有;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财产,在具体处理时,应当按照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分割,适当照顾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
如果经审查,事实婚姻关系没有被法院认定,属于非婚同居关系,则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的财产处理。因为同居关系不同于合法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夫妻共有财产关系是基于配偶身份而产生的,法律强调的是身份关系,并不要求夫妻双方付出同等的劳动、智力才能共同所有,对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如果查明属于按份共有关系,则按照各自的份额分享权力,如果查明属于共同共有的关系,则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正因为同居双方不具有配偶身份关系,所以,他们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并不当然享有共同所有的权利,一方的收入另一方无权要求分割,一方继承的财产另一方也无权享用。
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个阶段一系列的修改和完善,其实本质上是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和对新型矛盾的解决。但是,通过事实婚姻的脉络发展,我们可以也看出,“事实婚姻”制度却有其内在的矛盾性。站在民法当中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高度来分析事实婚姻的性质,事实婚姻只不过是一种不成立为婚姻的非婚同居。我国对“事实婚姻”的婚姻法律效力的相对承认以及将其作为无效婚姻处理的立法都是“事实婚姻”本质的违反,形成法律制度的内在的矛盾。而在刑法中对事实重婚的处理,又造成了一种在婚姻法上无婚可重,无婚可离,而在刑法上却有婚可重,有罪可定的局面。
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事实婚姻”的立法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我国这种“事实婚姻”状态并不少见,而且原因复杂,有因为是边远山区不知登记或者是由于登记不方便或是费用过高而未登记的农村青年,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经济条件不错,但追求自由,不愿意过多受束缚和承担责任的都市白领,而他们之中不乏将婚姻看得神圣,需要在物质条件具备和生活适应后才登记的青年人。
除此之外,老年人再婚时为避免财产纠纷和儿女反对原因也选择了这种非婚同居的状态。
正常运行的婚姻,是民事主体社会关系的压舱石,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但同时,存续基础被破坏的婚姻,又会反过来束缚个体的正常社会生活,乃至形成对社会和谐的潜在威胁。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的俗语,体现了对婚姻退出的慎重;但在当今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部分婚姻的解体已然不可避免。“事实婚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老一辈人的慢慢离去,其也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国目前对“事实婚姻”的态度,体现了“重家风”、“固人本”的精神内核,能够为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调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助力。
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
摘要: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婚姻礼仪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和探究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感知古代男女间社会关系的文化特征及其发展脉络。
关键词:婚姻制度;社会规范;中国古代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婚姻具有非常神圣而庄严的意义。《易系辞》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认为男女婚姻是承载天地阴阳之性密合而成。《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所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算为五伦,而伦常礼制、社会规范都是基于婚姻制度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古籍中也早有关于婚姻内涵的记载。《礼记·经解》郑玄注:“婿曰婚,妻曰姻”;《说文解字》解释为“:婚,妇家也”“、姻,婿家也”,都说明了婚姻具有严肃的伦理学意义,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婚姻礼仪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和探究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感知古代男女间社会关系的文化特征及其发展脉络。一、婚姻的几种发展模式在漫漫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我国的婚姻制度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从早期的原始群婚模式一步步走向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一夫一妻制度,见证和审视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发展模式。
原始群婚。原始群婚是人类早期祖先进行的一种两性偶合关系,古语曰:“其民聚生野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古代人们露宿野外,群居共生,男女之间的交往没有任何的规定和约束,也没有明确和固定的配偶,完全处于一种自然奔放状态,“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远古时代原始群婚的现状甚至产生了一些民间传说,比如《诗经·商颂》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男女无别、媾和无禁的自然婚姻状态。
血缘婚姻。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原始人群逐渐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集团部落,并且渐渐以血缘家族的形式作为识别标准。古人认为血缘家族中父辈和子女之间是不能够通婚的,但是兄妹同辈之间是可以通婚的,由此构成了血缘婚姻。关于这种婚姻制度模式,中国的古籍文献中也有相应记载传说,比如《风俗通》中就介绍了女娲和伏羲之间的关系,说女娲其实是伏羲之妹,兄妹两人是联袂成婚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在后世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人们能够看到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造型,而“两尾相交”正是夫妻媾和的特别象征。
亚血缘婚。亚血缘婚又称为伙婚,此种婚姻与血缘婚姻的最大区别就是血缘婚姻只是禁止父辈和直属下辈之间进行通婚,而伙婚除此之外,还禁止同辈兄弟姊妹之间产生婚姻关系。伙婚制的最大特点是兄弟可以共妻,姐妹可以共夫,但这个“妻”或者“夫”必须是外族人员,比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时都嫁给了舜,体现了伙婚制度下姐妹可以共夫的特点。亚血缘婚有利于自然选择婚姻配偶,这对于提高人口数量和质量意义重大。
基于此,古代中国人才有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深刻认识。
对偶婚。对偶婚是介于亚血缘婚和后期专偶婚之间的一种极为脆弱和不稳定的夫妻关系。在此种婚姻模式中,夫妻双方并不是以良好的感情为基础,而是以个人方便和需要为基础,通常是以物品交换的形式达成夫妻婚配,或者通过武力抢夺的方式得到配偶。这种婚姻模式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男子成为家庭生活维系的主要支柱,但由于男性数量可能在野蛮的战争中大量消耗,因而导致女子只能“暂时或长久地同一个男子结婚以作为解救的办法”。因此,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是相当脆弱和不牢固的。
专偶婚。专偶婚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这种婚姻制度的产生,是以父权制完全取代母权制,以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根本基础的。正是因为如此,专偶婚制度自其产生之时起,就充分表现出了男权至上的特点。而且从婚姻关系角度分析,专偶婚比对偶婚显然要牢固和持久得多,这也符合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因为儒家强调“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二、婚姻中男女地位差异在古代中国,婚姻本质上体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两性关系,反映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迁,而这个在男女地位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古代强调“男女授受不亲”,也就是男女不能同饮酒席,不能杂坐闲聊,不能同时出行,两性之间的界限是相当分明的。
两性之间结合为婚姻之后,依然在男女地位上显示出极为不平等的一面。
古人认为婚姻是家庭的大事,《礼记·昏义》云:“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礼记·经解》云:“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自进入父系社会之后,男尊女卑逐渐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易·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些文字概括让人感觉男尊女卑似乎完全是一种自然法则,是万万不能违背的金玉良言。其说法之一是由于丈夫获得了家庭经济的绝对支配权,自然而然好像也就获得了对妻子的绝对统治权。《礼记·郊特牲》说:“男帅女,女从男”,古语云“: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这些都是婚姻关系中女性地位卑微低下的真实写照。
到儒家思想占据完全主导地位时,其对婚姻的态度是“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并且以“三纲五常”等社会规范来约束夫妻关系,特别是约束女性的行为习惯,对夫妻之间的“情”与“爱”则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按照儒家的封建礼法制度,妇女应“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也就是说,妻子在家里只能遵守本分,操持家务,照顾子女,奉养公婆,没有任何经济地位可言。《仪礼丧服》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汉代刘向和班昭分别著有《烈女传》和《女诫》,引导女子要“以专一为贞”,信守“四德”(即妇德、妇容、妇言、妇功),后人将“四德”与“三从”合并为“三从四德”,作为妇女言谈举止中应该遵守的基本礼仪。另外,中国古代婚姻中对女性的贞节观要求苛刻,从各方面钳制和规范妇女的个人操行,要求她们守身如玉,容不得半点瑕疵,夫妻之间女性个人兴趣和志向的稍微外露就可能引起男性的斥责与惩罚。事实上,婚姻关系自其形成之初,男女之间就已经处于明显的不平等状态,束缚于贞节道德礼教之下的古代妇女,早已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可言,只能忍声吞气、唯唯诺诺。
此外,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夫妻之间婚姻关系的解除也要遵循一定的陈规陋习,而女性此时的地位更是日薄西山,江河日下。在夫权至上的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关系的解除主要由男方的意志随意决定,因此古代将离婚称之为“出妻”或“休妻”,而遭受遗弃之妻则被称为“弃妇”。丈夫如果要遗弃妻子的话,来自家庭和个人的理由可谓是随手可得和易如反掌,只苦了那些弃妇们的余生,大多数只能是孤灯瞎火,孤寂落寞,清贫甘苦,了却一生。
比如《孔雀东南飞》中描述的焦母逼迫焦仲卿无论如何都要“出妻”,其提出的理由竟然是嫌弃儿媳“不顺父母”,最后导致焦、刘两人双双殉情而死,为后人留下一声叹息;又比如宋代大诗人陆游本来与前妻唐琬一往情深,生活甜甜蜜蜜,但就是因为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琬,而陆游又对母亲非常孝顺,并且言听计从,最后只能被迫与唐琬相别分手,为此陆游直到晚年仍悔恨不已,心存遗憾之情。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时历代的婚姻制度多以巩固和维系父系家长制的绝对权威为原则,特别是允许男子“一夫多妻”,体现出对女性地位的压制和约束。比如《唐律》就明确规定男性纳妾是完全合法的行为,《明会典》也特别规定“:庶人四十岁以上无子者,许娶一妾。”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习俗主导下,自先秦时期到民国末年,上由达官显要下至市井小民,纳妾制度历经千年长久盛行,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中的一个顽疾。
